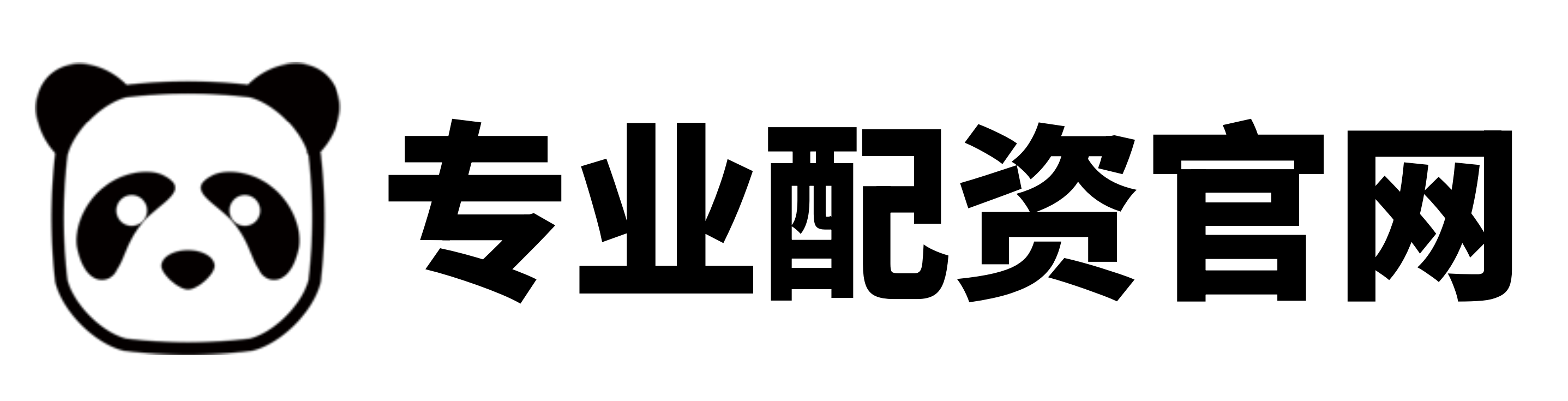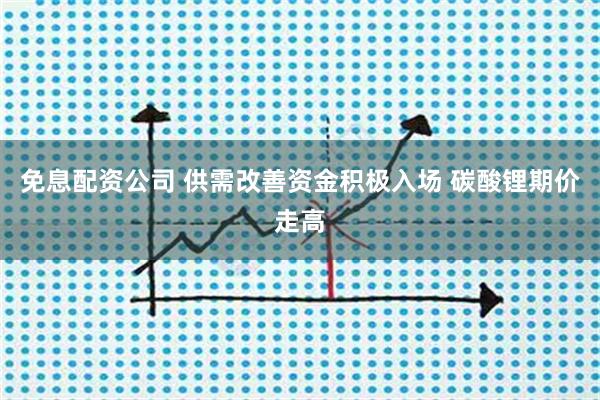免息配资公司 此人曾出言挑衅鲁迅,为了40元津贴甘当汪伪喉舌,才女林徽因还因他登报改名

1928年初秋的杭州西湖畔免息配资公司,暮色渐沉,微凉的晚风轻拂过湖面,泛起层层涟漪。湖畔的六角亭中,一位面容清瘦的青年正独自静坐,他便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林微音。只见他颤抖着将一叠被退回的稿件投入石桌上的铜盆中,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他阴晴不定的脸庞,眉宇间尽是郁郁不得志的愁绪。
就在这落寞时刻,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信步而来。为首的正是日后名震诗坛的戴望舒,身旁跟着他的挚友杜衡。他们被亭中这个焚稿的孤独身影所吸引,便上前攀谈。三人从文学创作聊到时事见闻,竟发现彼此志趣相投。戴望舒尤其欣赏林微音对文字的独特感悟,当即引为知己。自此,这三位文学青年便常常相约湖畔,谈诗论文,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然而命运弄人,谁曾想这位初露锋芒的文坛新人,竟会在日后为区区四十元津贴而沦为汪伪政权的御用文人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,林微音虽才华横溢,却因出身寒门、人脉匮乏,在文坛举步维艰。他白天不得不去银行做着小职员维持生计,夜晚则伏案疾书,可换来的却多是退稿的打击。每当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被退回,那种怀才不遇的愤懑便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
展开剩余78%幸得戴望舒与杜衡的提携,他们常在文人雅集上引荐林微音,使他得以在一些小型刊物上发表文章。1933年,他与富家公子邵洵美共同创办绿社,这才算是在文坛站稳了脚跟。林微音的作品以唯美婉约见长,字里行间流淌着细腻的情感,其文风之柔美竟让不少读者误以为出自女性手笔。这个美丽的误会甚至惊动了徐志摩、戴望舒等文坛名流,他们不得不屡次出面为其正名。
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由于名字发音相近,林微音常被误认为是当时已声名鹊起的才女林徽因。为此,林徽因不胜其扰,甚至召集好友商议是否要改名以正视听。不久后,报纸上赫然刊登了她的更名启事:徽音正式改为徽因。她在私下坦言,不怕别人夸赞林微音,就怕别人说林微音的诗作能与她比肩。
这番言论让林微音颇为难堪。生性倔强的他非但不退让,反而在《申报》上发表文章暗讽:若有人登门相求,改名亦无不可。言下之意是要林徽因亲自来求他才会考虑改名。林徽因读罢勃然大怒,认为此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,遂下定决心彻底与其划清界限。
林微音早年曾有幸结识鲁迅、郁达夫等文坛巨匠。初见鲁迅时,他被先生渊博的学识所折服,执弟子礼甚恭。然而短短一年后,这个曾经恭敬的后生竟在报刊上对鲁迅大加挞伐,言辞之激烈令人咋舌。面对这番挑衅,鲁迅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道:讨伐军中最低能的一位,也不过是一匹'叭儿'罢了。这番犀利的讽刺让林微音非但没能借此扬名,反而沦为文坛笑谈。
生活的重压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林微音。在那个动荡年代,微薄的稿酬难以维持他追求的小资生活。为排解苦闷,他渐渐染上了鸦片瘾。好友施蛰存回忆,曾多次深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,开门便见林微音神色慌张地借钱,每次只要三块大洋。起初施蛰存不明就里,直到后来才知这些钱都被他拿去地下烟馆消遣。本就拮据的林微音很快便债台高筑。
为维持烟瘾和生计,他不得不大量炮制粗制滥造的文字换取稿费。文坛同仁开始指责他为了金钱出卖文人风骨,他的声誉每况愈下。1939年,走投无路的林微音做出了人生中最具争议的决定:接受汪伪政府每月四十元的津贴,创办了为伪政权摇旗呐喊的《南风》杂志。
这一选择让他众叛亲离。昔日好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,戴望舒更是公开表示与此人再无瓜葛。有人痛斥他出卖文人操守,也有人同情他是为生活所迫。无论如何,《南风》的出版彻底坐实了他文化汉奸的骂名,也加速了林徽因改名的决心。
1951年伪政权覆灭后,林微音的生活陷入绝境。失去经济来源的他求职屡屡碰壁,连中学英语教职都求而不得。旧日友人避之唯恐不及,生怕受其牵连。晚年的林微音似乎有所醒悟,他在给老友的信中提到已戒除鸦片,并对过往行为表示悔意。几位故人试图帮他联系出版社,希望这位才子能重获新生。
但命运没有再给他机会。1982年冬,有消息称林微音在贫病交加中孤独离世,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伪文人的骂名。他的人生就像西湖畔那盆焚稿的火焰,曾经炽热,最终却只余下一地灰烬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华林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